来康平的外地人,稍有逗留便会发现一个奇怪而有趣的现象,一连走过几个、十几个村庄,它们的名字也许都无一例外叫窝堡。那些来康平乡下搞农副产品收购的商贩们,更会有这样的莫名感觉,走入一个又一个庄子打问其名,得到的回答极为雷同,形成了一长串的排比式:李家窝堡――刘家窝堡――沈阳窝堡――杨大保窝堡――韩达子窝堡……康平何以这么多窝堡?它有诱人的故事吗?康平人怎样看待家乡的名字?有必要来一番刨根问底的追索和考证吗?如果读者感兴趣的话,我首先告诉大家:康平的重要文化历史就是从这些窝堡开始奠基的。

一
从北方大都市沈阳去康平,仅百多公里,高速小车只需一个多小时便可抵达。然有一关口成为必经之地,否则,虽然条条新路可抵康平,却免不了会绕上半天一日,让驾驶者和乘客苦不堪言。
必经之地为法库门。法库门对康平如此重要为外地他乡之客颇生疑惑,不把法库门与康平的渊源关系弄清楚,就难懂其中的奥妙。其实,法库门是古代界定康平地理方位的一个关键性标志。北出法库门,柳条边寨以外,那星罗棋布的大小村庄便都是康平的了。东以辽河为界,北至内蒙古沙丘高原为止,西以辽西丘陵阻隔为限,这一片土地,历来为人们所褒贬不一。且看:“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有人说南北朝民歌中的诗句是描写康平的。“一出法库门,只见牛羊不见人”。一幅古代水草丰美,畜牧兴旺的图景,以稀少的人口,放牧管理着群群牛羊,拿现在的眼光看,也是科学发展观的时髦典型。而接下来的一句是:一过法库门,一半牲口一半人。这句顺口溜儿,康平人就难于接受了。这分明是鄙视康平人,把人和牲口掺和在一起相提并论了吗。因为这句话,康平人总是跟那些口有不敬的人打嘴仗,讨说法,争个是非清楚才肯罢。其实,康平土地的肥与瘠,康平人的荒昧与文明,不可能一句诗、一句顺口溜儿所能概括的。
据考古工作者的地下发掘考证,康平地域早在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即有人类活动,青铜时期已有人类居住,至辽金时期,康平地域已有相当人口定居,有些繁盛景象了,而由于战争和蒙古诸部的侵扰掳掠,元末至清初200多年间,康平地区又陷入人烟稀少的荒芜状态,直至清朝中叶的鼎盛时期,村落才渐渐稠密起来。
这种沧桑之变是有其历史背景的。
清王朝在北京定都后,对东北满族属地实行圈禁政策。满清政府还算体恤民情,一想修几千里的长城太劳费民力,就简单些吧,西起山海关,经锦州北镇再经法库镇北到开原威远堡又折向丹东凤凰城,划好路线,挖堑壕培高四、五尺,阻断车辆通行。为防止行人偷越,又在壕上密插柳条,待柳条成活,长成树荫,拿树枝子于树干间穿插编别,成为一道杖子,一条密实的柳树墙寨便形成了。一道柳条边寨把康平抛在边外,人家法库、新民在边里大搞开发耕种,干得热火朝天,康平地界则成为蒙古三王领地,寥若晨星的村落,守着王荒之地,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边寨在法库设一边门,农牧人出入,蒙古贵族进京朝贡,必由边门通过,由把守人员发放通行证件并接受检查方可通过,一旦有人偷越墙寨,要受到严厉处罚。在漫长的封禁时期,康平成为蒙古沙漠以外的标准牧场。
到了清中叶乾隆、嘉庆时期,随着清皇室政权的日益巩固,满蒙关系日益亲密,朝廷回过头来看,也没什么了不得的大事,防贼似的防着蒙民入内,也影响兄弟民族的感情,遂逐渐开禁,允许边寨内外自由往来。政策放开,蒙古王公拥有大片属地,开始招募流民垦荒。恰逢关内连年遭灾,直隶、山东一带广大农民纷纷破产,大批农民被迫“闯关东”,涌入东北。那股热潮比之今天内地人员趋向沿海要来得更为猛烈。试想现在人们向沿海涌动,是为了寻求更为富足优越的生活,而当年“闯关东”的人们是为了活命啊!那些推小车、挑担的强壮汉子,担筐里挑着孩子,脚后跟着女人,日夜兼程赶来,山海关外,到处可以落脚,但逃荒的人们还是相信前头有更加肥沃的黑土地在等着他们。可是挑了一程又一程,能占脚的地方都有了人家,继续向北,结果把担子挑过了盛京,一咬牙又来到了法库门,站在边门寨墙向北一望,哇,好开阔的地方!只见晴朗朗的天空下,漫岗平川,沃野连绵,碧草齐腰,牛羊群群,只是少有开垦的熟土。闯关东的汉子们有的是力气,还愁生荒种不出粮食,便一股脑地涌入这片荒芜之地,寻找心仪的地方搭窝棚建房子,村落便渐渐形成了。
清朝历史上,满蒙通婚极为普遍,很多皇室公主下嫁于蒙古王公贵族的后裔。固伦雍穆公主出嫁时,边外一块上好的膏腴之地做为陪嫁划给了她的名下。光有土地是不够的,没有人才也不能够很好地开发和经营,于是做为陪嫁的一批人跟随到这里落户来了,不过这些人不是普通的农人,都是些可以各操兵刃的手艺人,什么木匠、铁匠、石匠、瓦匠、皮匠、机匠、豆腐匠……行业多得是,统称为七十二行匠人吧。他们的到来,为后来康平的开发和社会进步,无疑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他们也没有更多的文化知识,甚至很多人都是目不识丁,但他们手中有技能,所以格外受到青睐。
蒙古贵族也看好了康平这块土地。他们一次次骑着草原骏马在这里兜圈,是看定了这块土地的风水。北起科尔沁沙地的博王府纵缰奔驰,直到盛京沈阳,出了沙漠再入辽河平原,一抹缓漫的平川地,只是在康平地界的南缘有一脉山水,王公们看好了这处唯一的山地做灵寝墓地,几代王孙埋葬在这里。功德无量的王爷们长眠在这里,得需要相当数量的守墓人户,于是又一拨蒙古姓氏的人群奉命迁来,守着陵旁,建村立户。综上这三种因素,使康平地域的人口骤增,村落很快遍布境内的角角落落。据地名考察统计,明末清初时,康平境内的村落还寥寥无几,而截止清末,现在的665个村屯中,已出现了641个,近百年来,仅仅新增了24个,大部分形成于清中叶乾隆、嘉庆、道光三朝。
现在,我们要追索一下,来到康平的这些先民们,当时在为村子取名的时候,有没有认真地动动脑子思考一下,召集全聚落户族家长民主商讨一下呢?现在看来,显然是没有这些程序的。你看那一个个村屯的名字,都是以姓氏打头,尾缀一个屯、街、店、窝堡等等。很显然,谁家是聚落的原始首户,就以其姓氏命名,绝无二意。现在想来,当时,非但没有民主研讨,就连被命为村名的始建者本人也未想过起名的事情,张家屯、李家窝堡竟是被别人叫开来的。事情很简单,挑着担子闯入边外的一家数口,在荒野里选准了位置,挖土培壕,构木架棚,再苫草抹泥,筑成了简陋居舍,名为窝棚。若户主姓李,改日有另聚落的人来探视,回去便说,我去了李家窝棚,这个聚落地名就这样叫来叫去,便形成了。多年以后,聚落发展到几十户人家,李姓户主才回过神儿来,这屯子原来是以我家姓氏命名的,我怎么没有在意呢……
康平地名有多种称谓叫法,而以“窝堡”最为普遍。统计一下,全县村庄叫“窝堡”的竟有248个之多,而叫“屯”的才只有45个。要考证这些叫法,人们多以为是一种随意,并未觉出有什么深层意义上的区别和不同。而通过考证便找出一些规律来了,有地理环境的、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
康平地貌大体上分为三种类型交错相连,那么以地貌命名就顺理成章了。东部为辽河平原,遂有牤牛河、背河赵家、天鹅泡、泗河汀等近水地貌的名字出现;西南部为丘陵岗地,便有莲花岗、鸭蛋山、狐狸沟、星星沟等山地特征的名字;西部北部地靠内蒙古沙地,故有曲家坨子、潘家岗子的称谓,还有相当数量的蒙语地名间插其间。二牛所口、沙金台、东西扎哈气、西二喇嘛、五汉朝老等,据考都是蒙语的转音。地理环境的不同而影响聚落的名字,这是很自然不过的事情,而“屯”和“窝堡”又有什么区别吗?首先说屯,它们在康平多分布于东南面靠近柳条边一带,或是大道经过的沿路一线。这些地方,既不是坡陡石多的山地,也不是低洼盐碱的甸子地,都是一色的平川漫岗的膏腴之地。屯即有军队或官方差人屯驻的意思,实际上,这一带恰是跟随公主陪嫁前来的匠作杂役之人聚居的地方。看来“屯”的起点就比其他的地方高了一筹。
诸多叫法中,“窝堡”是最为寒酸的了,窝堡是早先“窝棚”二字演变过来的,多为挑担闯关东的迟到者,被统治者称为流民的关内户,肥沃之地岂敢奢望,看看好地方已被占尽,肩担远足,力已耗尽,捡个沙包碱洼之地栖居下来。这些聚落的形成,无疑凝聚着祖先们逃荒迁徙过程中无限的艰辛、凄苦,甚至是血泪斑斑了。辛酸的窝棚在康平的文化历史上极具代表性。过去,外地人评价康平,找出康平人许多缺点,落后、散漫、进取意识差等等,这些性格缺失,在那些寒酸的窝棚里找到了文化积淀的根源,那些窝棚就是昔日康平面貌最为典型的写照。当然这都是古代的历史,在那些窝棚里,子孙繁衍正旺的时候,康平还没有建县,一个稍大些的聚落只管它叫康家屯。直到1880年(清光绪6年),朝廷颁下诏书,批准划边墙以外、辽河以西的广大地区建县,辖区面积很广,有历史记载的区域面积为6100平方公里,连当时很有名气的吉林省的郑家屯、内蒙古的金宝屯当时都划入了康平的版图。于是,那些屯、窝堡等村落悉数为康平县管辖。从此,康平才以县一级的建制,统管一地,相延至今。
二
康平的“窝棚”演变为“窝堡”,想来是官方所为。康平建县以后,那些县令、县丞们统揽民生、登记户簿,在聚落名称上肯定遇到了一些麻烦,其他称谓倒还可以,这个“窝棚”却极不顺眼,官方用来也极不规范。窝棚一词从字面上来看是个体指代,只能说它是一幢非常简陋矮小的屋子,涵盖不了整体居落,把“棚”换成“堡”就顺理了。所以,后来在官方行政管理中,出现了“窝堡”二字。
窝堡的“堡”字,汉语拼音为bu,有人不加区别地用铺(pu)的发音是不准确的。“堡”字在汉语字典里三个发音中,一为城堡(bao)的堡,二为三十里堡(pu)的堡,这二种解释都不适用于辽北,唯有“补”(bu)的发音才更为切合,各类新老词典,都把“堡(bu)子”一词解释为:围有土墙的城镇或乡村,泛指村庄。也唯有这种解释才与康平地域环境文化历史最为妥帖。
康平的堡子都不是很大,百八十户、四五十户、二三十户不等。方整的农家小院,以界墙相隔,户户相连构成了村落。小院和房屋,早年都是土的。土屋的墙壁有两种筑法,一是和泥垒垛,二是湿土打压。泥垛的墙不能一次完成,并有中途坍倒的危险,故湿土打压的办法常被农人们采用。在村外选有粘性或碱性的黄土,用畜力车拉来院内,在筑墙的位置上,将长长的一副木板条,用立木夹起来,形成槽体,众人挥锹往里填土,几个壮汉早在板槽内踩实踏平,遂双手高高举起石蛋蛋,发狠力猛的向下砸去,石蛋的印痕如密密的针脚,一个接连着一个深深凹沉下去,几位壮汉轮流下来,一层土夯实了,众人再迅速填土,几位壮汉再一次挥石密轧一遍,一板墙完成了,再上一副墙板,填土夯轧完成后,底下的一副墙板撤下返上来,轮番叠加上去,墙体一点点升高。为使屋墙结实耐久,每填层土要铺撒一些短柴草,保持墙体的拉力,又在夯击时不致使粘土粘住石蛋。一面墙够了高度,转向另一面,一副完好的四壁墙框立起来了。待改日选个吉祥时辰搭上梁檩,棚上屋顶,安上粗制门窗,一座土屋宣告竣工,主人便可搬入新居生活了。整个工程要耗费劳动工日百十左右,各项用料再加吃喝费用,是要积攒多年的。农户把盖房看作是人生最为艰难,也最为荣耀的头等大事。哪家建屋动工这天,整个屯里的劳动力全数前来帮工,几挂畜力马车也都赶来运土,众人的吵嚷欢叫声,石蛋落下的砰砰声响,车马往来嘈杂四起,真是热闹无比。特别是在高高的正在夯筑的墙体上,那壮汉把石蛋高高举过头顶,浑身的肌肉拧成了紫铜色的疙瘩,一腔的气力喊出一声“嘿”!石蛋猛然击落下来……那种记忆,在人们的脑海里,早已形成了一尊雕像,至今挥之不去。
房屋,简单的结构,泥土筑垒,岁年须精心泥抹,保其夏雨不漏,严冬避寒。早春,大地刚刚化开一层土皮,农户人趁农闲开始抢挖碱土,拉回院内,担水和泥拌“羊搅”,三四个壮汉要一天时间才能抹完屋顶,四周墙壁还须一天,有下屋的人家还要增添工时。这项活计很苦重,汤汤水水的泥巴,要用锹叉甩抛到高高的屋顶,又要手持抹板用力将泥巴摆平,抹个致密光滑漂亮,一日下来,壮汉累得腰酸腿软,腕肘麻木。农人谚语:造屋抹房,活见阎王。几日的泥水脏苦,小屋焕然一新,主人脸上也焕发了喜气。屋墙一层皮,为它罩上了新衣,主人脸面也光彩呀,好像娶了新妇一般,进出院门,一身轻松,劳作起来心情格外畅快。可是,从春到秋,大雨小雨不断,几场暴雨泼降下来,泥屋便凋颜鄙貌,颓然而无精打采的样子,变得非常丑陋,又须来年一连几日的劳苦了。
泥屋有火炕。火炕的大小,凭房子的面积而裁定。两间房子僻一间做厨房,叫外屋,里间为寝室,临窗的南面就被一铺火炕所占据了。若三间房子,仍作“口袋式”结构处理,就有了两间寝室,火炕也继而成为连二大炕。火炕供农家人休憩就寝之用,温热而持久,世世代代为庄稼人养育了一副铁骨铮铮的好身板。特别是到了冬季,乏累一天后,平卧于烙热的火炕,腰背四肢舒舒服服地渐入梦乡,睡的熨贴而满足,天明一觉醒来,浑身筋骨轻松无比,那种享受,是世居城内睡床的人无法想象的。
火炕为农家人生存所必需。世代生息于此地的土著人所沿袭下来的生活方式,都是经历史验证过的,必是有它无所替代的价值。从古至今,多少风俗文化习惯被改革、甚至取缔,而火炕一直沿用下来,也许再过一个世纪仍会依然吧。
东北农家普遍居寝于火炕,而各地区的火炕又有质的不同。居于山区,采石料作炕,巨大片石作炕面,加厚泥,石料撤温快,而厚泥炕面却保存了热温。较早产砖的地方以砖作炕,棱角方整,便于操作,炕面也易于找平。而康平少山,用石短缺,红砖生产则是较晚的事情。早年用泥土打坯作炕,便是康平的一大特色了,就地取材的泥土,康平总不会缺少。表土为黑土耕作层,往下挖去即为细腻的黄粘土质,遇雨水变作胶一样的粘着,待晾晒干透,便坚硬如石。
当年,在农家存放农具的屋子里,于昏暗的光线下,不经意间,你也许会发现土墙的钉橛之上悬挂着一只木制长方形框具,这便是制作土坯的模具了。打制土坯须避开雨季,一般在仲秋时节,雨水旺季渐渐淡去,秋日阳光仍很毒火,这便是最佳的时日了。现在回想起来,打坯是一项很好玩的工作,于村头上选一带靠近水源、土质上好的地段作坯场,家家摆开了架势,抢时打制。先将黑土层挖掉,见到了黄土,翻撮成堆,担水加铡过的短柴草,开始用力搅拌。同样和泥,却要比碱土抹房时费力得多。碱土和泥是顺滑的,而黄土是顽固透顶的那种粘着,没有几个回合的扒倒折腾是不会成形的。主人生怕“羊搅”与泥土不匀,挽了裤腿,赤脚入泥巴中一阵踩踏,再经翻扒,用镐头打腻一遍,坯泥总算柔合了。这期间,男人的做工总要有女人的指点。女人是凭厨上和面时的经验来指导男人,并亲自查验一次泥胎的软硬均匀,说一声好啦!男人便放心地上泥。而脱制过程一般由男主人来做,女人与孩子们只作帮手,端泥巴,供沿水。有经验的扠泥者,一扠子撮来,恰好是一块坯子的用量。男主人摆好木模子,在草地将泥胎滚了又滚,成一榄圆形的泥蛋蛋,双手捧入模里。木模四周先要撩泼少许沿水,以便提模时滑爽顺利,然后双手合拳在模里捶压一遍,表面用手掌反复抹腻,达到光滑,便轻松一提模框,一具完好的泥水坯胎便形成了。接下来留好间距,脱制下一个。一行一行的脱出来,一片不小的范围摆满了,过三五日,坯子佯干了,便逐块掀起,依次立于原地。酷似多米诺骨牌的情形。为防止其如骨牌那般连锁倾倒,遂摆成“z”字形,块块相顶,每行便形成了一条浪线状,煞是有趣好看。男主人欣赏了一阵子“骨牌”,很稳固,便带着好心情回家去。
此时,小院里的风景更加迷人。这时节,女人把家里所有的被褥全部拆洗了,用浆面浆好,正于小院内扯起长绳晾晒。秋日阳光好,是女人浆洗的好日子,一年的污浊只指望这个季节被浣洗干净,再重打浆面,浆揉一次。长绳上悬挂的里儿面儿,展示着诸多花色品种。月白、靛蓝、墨青、麻花,间或也有现代技术印染的细纹大花被面、褥单。那些色彩,每年仅有一次的展示机会。晾晒前,在女人的催促下,男人要将院内一切畜禽粪便、柴屑尘埃打扫干净,一道风景拉扯出来,小院显示出一派出奇的温馨,一股平日少有的文明气息弥漫于村庄院落,让庄稼人自己感叹,小院总是这个样子该有多好!
几日过后,小村之内打破了一惯的宁静,家家响起了棒槌声,那声声脆响,把妇人忧郁已久的心胸击打得亮亮堂堂,农家的窘困忧愁似乎全然不再了。在翻转锤石上的被面时,年轻的妇人见到了那床麻花被面,那是自己亲手摇车纺线,供土著织匠织就的土布,拿到康平县城街里的染坊,染成了心爱的麻花色。一直浆洗捶打了多年,时下虽有了现代印染,却也舍不得丢下。这里有她们的血汗,有她们对于堡子以外大千世界的追求和梦想,青春的意念早已织就于细密的布纹里了。
三
捋顺一下康平的发展历史,远古的不必赘述,只从民众建起窝堡,官方建县开始,康平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一定积淀了厚厚的文化土层。世人评说一个地方,能说出一些总体特征来,大体上也是从文化角度,所以说,文化冠盖的一个地区的面貌,是一个地方的形象。而地域文化是生活在此处的人来创造的,说一个地方首先就要评价这个地方的人。那么外地人怎样评价康平人呢?从各种信息来源上可归列出以下词语:老实、热情、真诚、倔强、坚忍、僵化、懒散、接受新事物慢……可能还有许多,把这些评语归纳一下,既有褒也有贬,这是情理之中的,不过康平人诸多的个性中,值得炫耀的并不多,而其中有些突出的个性,就只有倔强、坚忍了。
时下小品盛行,老实的康平人也学会了调侃,而最为精彩的一段口头小品便是:沈阳人有什么了不起?康平人哪点差?我们两家的祖先当年是结伴闯关东来的,担子挑到沈阳,他们的祖先身体瘦弱挑不动了,只好歇脚落了户,而我们的祖先,由于腰板硬朗,一鼓作气多挑出200多里,在康平扎了根!若是我们的祖宗当年也耍熊,落脚沈阳,如今我们也是响当当的城里人啊!这种说法作为小品可能引来一些笑声,但把它作为史实来考证,相信的人就不会更多了。不过评说起来,康平人性格坚忍倔强的一面还是世人公认的。
我的祖籍是山东寿光,曾祖父最早来闯关东,凭着一手织布手艺,在堡子里落户,成为人人尊敬的硬汉。他去世时,我的父亲才刚刚十几岁,我们只见到他的坟头排在最前位,他那闯关东的故事也只能是传说,而本家族里面有位八爷却是我们从小陪着他在堡子里生活过来的,印象极深。中等个头,敦实的身板,由于闯关东的年代较晚,满口山东语音侉调,直到老去也未能改变过来。据他讲闯关东的原因不是闹灾荒,是因为他给人家放牛,其中有一头牤牛极不驯顺,见人就顶撞,已伤了好几个人。一日他在野外放牧时牤牛向他撞来,他年轻气盛,手持粗棍,辟头一棒打来,牛当场晕倒在地,他等过半晌也未醒来,怕是死掉了,穷困之家哪里赔得起一头壮牛,便丢下牛群跑了出来。当得知那头牛最终缓醒过来了的时候,他已投奔康平,在叔父先期到来的滕家窝堡落脚了。八爷与堡子里的农人一样,过着纯朴坚忍的生活,日子也一步步富足起来,他的寿命很长,活到了94岁,前些年才去世。他看着新社会,领受着改革开放,还跨过了新世纪的门槛,他一生很知足了。然而让人难于理解的是,他自十五六岁来堡子,竟一次老家也未回去过。他不想自己的故乡?不想自己至近的族人?平时晚辈后生们也问过他,当时他只是长长地吁出一口气:“嗨――”!表情木然,口中却再也无语了。一个“嗨”把他一生一世的内心苦痛全都涵盖在里边了。没有宁死不回头的倔强性格,能忍受得住思乡的苦痛吗?没有坚持再坚持的忍受,作为拓荒的一代,别说一步步打造幸福生活,就是扎下根来也是很难的事。
再看那些最初命下村名的人户,后来的命运更为舛错。这些开荒占草时的名誉庄主们,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建户立村,只担了一个村庄的名号,由于创业早,生产积累丰厚些,成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在村屯堡子里,他们是倍受尊敬的,而土改时期一般都被划了高成份,不是地主便是富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日子都不好过。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产生了。小时候,我们从未对自己的出生地产生过骄傲,心里上有了深深的烙印,对那些窝堡始终怀有一种鄙视,心里总是疙疙瘩瘩,都在讨厌自己的出生地--那些窝堡们。你看,你是张家窝堡的,张家正是人人喊打的地主;你是李家窝堡的,李家恰是被天天批斗的富农,一个几十上百户的堡子,都是被时下整个社会厌恶的地主富农的姓氏所冠盖着。再说,那些“窝堡”往后一缀,土里土气让人难以扬眉挺胸。你看关里那些上了电影的杏花村、红石峪多美,最损弄个赵家庄、马家河子也比窝堡顺气。人们心里愤愤不平了,决心要改一改。怎们改呢?改掉前面的姓氏便失掉了匡限,一群窝堡哪得区分,整体名字全都取消另改新的,那么整个康平地方一片陌生,人们像到了一个怪异的他乡,七姑八姨居于何处都难于找到了。不行,改不得,地主就地主,富农就富农吧。倒是有一个时期,传统的村名在人们的口头上被简化了,办法是一律把窝堡去掉,李家窝堡就叫李家,赵家窝堡就叫赵家。这样一简化,倒省事许多,却也不伦不类。人民公社体制时期,我所在的生产小队是滕家窝堡西队,被简化为滕西队,本地人们明白是咋回事,而外地人听来只是一头雾水,我也感到了别扭。少不更事,难免想法离谱,一次为市报写的一篇报道中,把“滕西”改为“腾溪”,一经在报上登载出来,颇受人们的青睐。哦,奔腾的小溪,多么欢快灵动的名字啊。连发稿的编辑都认定了这是个山区小村,泉水叮咚日夜流淌的一个所在,来信说非要亲自来看一看,结果被我婉言拒绝了。看来一个地方名字的作用还真不小,不过引起歧义也够麻烦的,改来改去人们觉得还是不改的好。说到底它就是一个地方的文字标号而已,经过世代的积淀,遂成为一种史传文化。文化就像温软的水,经自己的耐性,可以把石头磨洗圆润光滑。而文化一旦形成,任何人为的政治力量都难于改变,这就是文化自身的力量。
“窝堡”二字终究没能被省略掉,而那些名誉庄主们的后裔却大都走掉了。土改乃至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那些地主富农们都要被当靶子,受尽了歧视,这是祖先们在荒野里立下首户时所始料未及的。又批又斗的景况难于再熬下去,结果,他们选择了再一次逃荒。他们都是弃掉亲手建造的房屋,连邻居也不敢打一声招呼,背着行李卷,于夜深人静时,默默告别老屋,偷偷上路的。想来好寒心,早年创业的功臣,此时他们的儿孙们为政治所迫,不得不告别地下的先祖,背井离乡另寻出路去了。康平人的去向多是松花江以北,嫩江以东的广大地区,当时叫北大荒,他们以盲流的身份,管自己的行动叫闯江东。早年那一拨是闯关东,现在又一拨闯江东,一个关东、一个江东,被逼无奈,步步向北啊!他们在那里又一次像祖先来康平时那样,搭棚立户,拓荒垦植,开始新一轮的艰难创业。有一点不同的是,他们所建立的村落绝不叫窝堡。都起了一个漂亮的名字。有一个几百户的大村落,百分之五十是康平人,取了个颇有文化含量的名字叫聚贤屯。一个时代过去了,北大荒建成了米粮仓,而改革开放后,政治和缓了,时代变得宽容了,而那些逃荒的人家,却绝少有迁回故地的。游走北大荒的人们啊,秉承了八爷们的倔强性格,创业在哪里,扎根在哪里。祖上有句老话,他们记得牢:好马不吃回头草啊!
四
1992年12月,一份国务院的文件批转下来,康平县重新划归沈阳市。看来就是一个规属问题,而就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而言,这是一个大事件,绝不亚于清光绪帝颁旨建县时的历史意义。
康平地方历史悠久,命运多有跌宕。除早年乱投其主外,仅建县后,地理沿革,行政区划的变动就有16次之多,重要的动态隶属变动有:1880年建县时规昌图府管辖;伪满时期属奉天省;1947年11月康平解放初始属辽北省;1949年5月,辽北省撤销,划规辽西省(省会在锦州);1956年属铁岭专区;1958年划规沈阳市;1968年重规铁岭专区,后属铁岭市;1992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康平县重新划归沈阳市。时代的变迁、地理沿革的变动,现今法库门外十公里左右一带不再是康平的地盘,北面的郑家屯、金宝屯一带也不再属于康平的版图,还划出了省区界。而行政区划无论变了多少次,康平的上属多为沈阳和铁岭。
凭心而论,康平与铁岭地缘较近,守着辽河两岸对望相居,同属辽北文化圈,多年相处,感情不薄。赵本山一夜走红,铁岭成为人人开心并向往的“大城市”,此时康平划归沈阳,似乎与此无关了,而赵本山一干人马在央视大台一亮相,侃一段小品,甩出一曲纯腔小调,康平人仅为行政区划的原因而无动于衷吗?那秧歌、二人转婉转的唱腔,那含着辽北土语方言的小品,听来就是康平地道的土特产品,怎么咀嚼也是一个味道。
而沈阳呢,康平与沈阳的关系,几次分离归属,渊源甚厚,只不过沈阳后来发展的规模越来越大,成为北方大都市,以沈阳为中心形成了都市文化,而康平依然固我地坚守着隅角里的纯朴和传统,与沈阳多年若即若离的关系,首先在文化上有所分野,人们在心理上产生一定的差距,这是自然的。而一但重新划归沈阳,依托大城市,康平的快速发展有了无限的前景。这是同根的兄弟又一次归伙团聚,不管怎么说,作为堂兄的沈阳,时隔多个世纪,仍没忘记康平,伸出手来拉小弟来了。只是归伙那天,埋怨了几句祖叔们当年的逞强,担子多挑出200里想避开大地方,乱世求僻静。今天逢上了盛世,一起联手再创大业吧!
上个世纪90年代初,电视剧《少奇在东北》剧组,来康平拍摄外景,这让康平人感到了极度兴奋和好奇。众人聚在县招待所,围堵追看特型演员郭法曾,而细细打问,人们的热情一下子降温了。为啥来康平?因为康平土房多,那些土里土气的窝堡,还有土里土气的房屋适合于剧情环境的需要。康平人知道了拍剧的缘由,顿感气馁,好长时间情绪低迷而沮丧。时间仅仅推移十多年,而现在呢,哪个剧组再要来寻找七扭八歪的土房子,恐怕不太容易了。过去,康平土地盐碱含量特别重。起初,古人来康平,每到春季要扫碱,凡有低洼处,便有白花花的碱片,人们挑着担子把含碱最重的土皮屑一担担运回家里,煎熬一气,形成个大大的碱坨子,把它叫做大碱,用它来代替苏打发面食用。而田野里,盐碱重的地块是不长苗的,为此,农人弃掉了好多土地。包产到户后,土地越来越被农民看好,很多荒碱地被开垦起来耕种。说来奇怪,农民翻一块种一块,块块都变为亩产千斤的上好良田,祖宗们即使从坟墓中醒来,万万也不敢相信,这就是他们开荒占草的地盘,哪里还找得到稍有片量的荒草和碱片,连沟沟汊汊都是绿森森的庄稼。看来,祖先们寄望的遍地良田的梦景终于实现了。土屋没了,用于养护土屋的碱地也随之消失了,座座砖石结构的瓦房替代了古老的土屋,间或也有小楼竖起来,祖宗们用过的弯把犁成为文人们到处寻找收藏的民俗古物,四轮农田机车出入万千农家,遍于田野耕爬。
名字还是祖先起的那些名字,窝堡却不是那些窝堡的原貌了,几代人口更迭,户数增多了,土屋不见了,红墙瓦舍,绿树掩映。更让人关心惦记的是,那些蜘蛛网一样串连着一个窝堡又一个窝堡的土路,还那么泥泞吗?
康平的地名中有很多叫店的,兰家店、李孤店、孙家店、候家店,考查者把它们串连起来,认定这是一条古道,盛京沈阳通往蒙古王府的通道。道边必有店家供旅人歇宿,后来以店聚起村落。村落形成了,名字亘古未改,而古道却早已废弃。改革开放后的康平,一条新兴的203国道,从沈阳始,穿越法库北门,贯穿康平南北,向北伸向内蒙古、吉林,直至黑龙江的明水;彰桓线省道横贯康平全境,连接东西两条铁路交通大动脉,还深入到辽东山区桓仁;新世纪的门槛跨越之后,铁朝高速公路先行建成通车,从昌图接近四平的干道接入,横贯康平全境,过阜新至朝阳,再入河北过承德直至北京。尔后沈康高速建成通车,继而,直线向北延伸到郑家屯、松原,直至大庆。看来康平交通很发达了。而康平的乡下历史上一直是泥泞着的,人行小路泥泞着,畜力木轮车、铁车、胶轮大车碾轧过的大道仍然是泥泞的。迈过新世纪的门槛,刚刚疾走了几步,康平乡村的泥泞,一夜之间几乎不再了。全国村村通油路项目,首先在康平开工试点,仅仅三年间,乡村道路脱掉了泥泞,光光的柏油路,让泥腿子农民洗去污浊,换上铮亮的皮鞋,象城里人那样,踏动脚步,欣赏自己脚后发出的脆响,很洋气的感觉,很有神采。跨上新买来的摩托一圈圈很有兴致地兜风,农田里无须传统笨拙的辛劳,青年农民到新落成的北方塑编城打工挣钱,成为上班族的工人。早晚闲暇时光到村里的文化广场里去,散步、休憩和游乐,有了城里人逛公园的轻松愉悦。
在贫穷落后苦苦奋斗的岁月,康平人曾有过恶毒的咒祖言行。由于地域环境的差异,当时康平看不到希望,寻不到出路,一致认为今人落到这步田地,先人是有责任的,首先归咎于祖先。而后来康平人终于想通了,光埋怨祖先有用吗?他们当年在这里落户容易吗?今天的我们有没有责任呢?祖先的使命是在这块土地上扎下根来,我们的责任是如何建设好家乡,不然儿孙后代不也会如此来埋怨咒骂我们吗?
现在,康平乡村建设有了今非昔比的变化。房舍、道路、村屯环境,也包括人们对于家乡名字的坦然心理。那些窝堡造就了康平人不畏艰难、奋力开拓、打造全新生活的铁汉精神,而这种精神如今已成为了康平人可贵的一笔文化遗产,他们要拼力守住这可爱的精神家园,这是他们发轫的根,当这块古来一直落后的地方完全进入小康社会的时候,他们也忘不了深情地呼唤一声:
哦,遥远而可亲可爱的窝堡……
2006年7月初稿
2007年11定稿
2017年结集再次增改校订
作者简介:王甸葆,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康平县作家协会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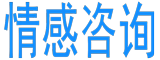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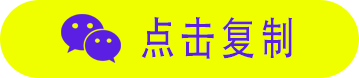




评论列表
文章我看过,感觉说的挺对的,有问题的话可以多去看看
如果发信息,对方就是不回复,还不删微信怎么挽回?
发了正能量的信息了 还是不回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