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24小时客户端-钱江晚报记者 张瑾华 通讯员 马正心
2 年前的一天,作家苏沧桑打点行装,深入老家台州一个草根戏班,与“做戏人”同吃同住同演戏,写就了三万字的长篇非虚构散文作品《跟着戏班去流浪》,2018元月发表在第1期《十月》上。
2年后的今天,《跟着戏班去流浪》荣获《十月》杂志主办的第三届琦君散文奖。她说,她要特别感谢带着她流浪的临海吉祥越剧团沉香般美好的姐妹们,这份荣誉同样属于她们。这个作品,也是苏沧桑在《人民文学》2017年第5期头条发表的非虚构《纸上》的姐妹篇。
那期《十月》的《卷首语》中写道:作家苏沧桑文章真实地记录了特定人群的生存状态及思想情感,其真切、细微的描述,远非躲在书斋中所能完成。我们身边被忽略的现实人生,在文中挣脱了概念化的存在,变得如此鲜活且意味深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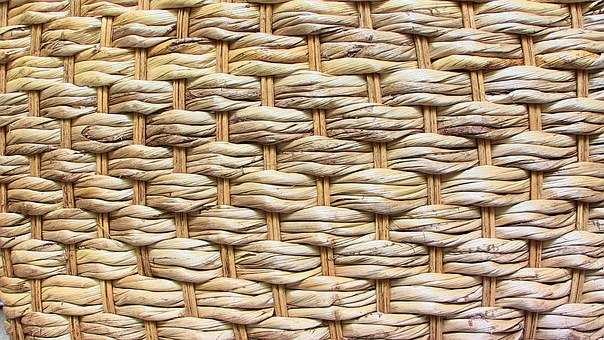
这两年,苏沧桑走向民间的脚步并未停下来,似乎正兴致勃勃地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不能回头了。她说,“接下来,我还想去做湖笔,养蚕,放蜂等等,书写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美,劳动之美,人民之美。”
深入越剧草根戏班一个月,深度体验原生态民间戏班生活。她的《跟着戏班去流浪》分“路遇、戏痴、嘟嘟、住处、小生、吃饭、扮上、唱起、拆台、过台、封箱、官人、重聚、曾经、沉香”,共15个小节,3万字,讲述大时代小戏班底层人的故事。
她回忆,自己是在人生途中遭遇了一些灾祸后出发的。“出发两个月前,我遭遇飞来横祸,头破血流,紧接着因闻所未闻的十二指肠憩室炎住院,五天五夜水米未进,虽侥幸未动刀,却也折腾得死去活来。身体虚弱的人,想法便少了,原本在意的一些事一些人便淡了,沉睡在心里很久的梦,便醒了,逸出来了。”那些逸出来的东西,“跟着戏班去流浪”,就是其中一个。
“连续四天大雨,把天都下漏了。我的身体也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状况,一阵冷一阵热,头顶已经愈合的伤口隐隐作痛,隔几分钟,整个头部从耳朵开始突然发热蔓延全身,心跳加速,气喘不上来,浑身无力。我母亲劝阻,说你病刚好,元气还没补上,太虚弱了,腿上又被蚊子叮了那么多毒包,天这么闷热,雨这么大,戏班里那么苦,不要去了,等身体养好了,秋天再跟她们去吧。但我还是去了。”
为什么偏偏要选择“戏班子”呢一头扎进去呢?
那是2017年芒种后的第一场黄梅雨里,苏沧桑和父亲吃过晚饭,她上三楼收拾“流浪”的行李。她记得三楼面山朝南的卧室,曾经睡过四个人——四个做戏人。三十多年前的冬天,村里请来戏班做戏,小旦小生等四个主要演员被分到她家里。小旦微胖,面目模糊,声音甜美,小生以极其俊美的扮相和极富魅力的唱功做功,一夜间轰动了山后浦村。她每天心跳最快的时候,是看到扮上戏妆后的她——她扮演的所有角色都像我梦中的白马王子。
苏沧桑深情写到了这一段自己从小与越剧的缘份——
“我是戏痴,我的祖辈更是。月圆之夜,小渔商贩出身的祖父常雇一条船,在楚门镇南门河等青灯古、赖乌丁等一帮“狐朋狗友”一一上船。锣鼓笙箫三弦京胡一应俱全,却没有女人。祖父拉京胡,他们自弹自唱,开怀畅饮。夜半尽兴后,祖父哼着小调走在清冷的石板路上,一手烟斗,一手提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带给祖母吃,他知道她会一直等他。
祖父浪漫的基因,流淌在二伯和父亲的血液里,也流进我的血液里。儿时的二伯演过《野猪林》里的林冲,儿时的父亲演过《血泪仇》里的伪保长,没有戏服,用窗帘布当披肩,借庙里神祗塑像的龙袍当戏服。儿时的我将越剧《红楼梦》看了七八遍,并无师自通学会了几乎所有越剧经典唱段。儿时的木雕床底下,珍藏着我自己缝的一个小姐布偶,鞋盒子做成她的闺房,中间用锦旗的黄色流苏隔断,用黑线做的云鬓,从母亲的珠钗上偷拆了两颗珍珠做的步摇。在我眼里,她是林黛玉,是祝英台,是《碧玉簪》里的李秀英,是《柳毅传书》里的三公主,是寡言的我……她是有生命的,她与孤独的我自成一个宇宙。
“十三岁那年,从小镇搬到山后浦村新家时,她丢了。我想,在某个幽暗的角落里,她已经成仙,她不愿离开那间快要坍塌的老屋,她的道场。我想,有一天,她会以另一种形态回到我身边。”
她回忆,小时候曾经有个疯狂的念头,就是跟着戏班子走。没想到这儿时的梦想,如今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这个苏沧桑老家玉环的戏班的名字叫“吉祥”。她身体跨出去后,她跟戏班子同吃同住同演戏,体验到了封箱时的悲欢,觉得戏班子里的他们太不容易了,也太可敬了。
农历五月二十一,是吉祥戏班封箱日。
“我原想说,做戏多自由浪漫多开心,可短短几天,我便明了戏班生活的本质绝非原先想象的那么美好,而是极度的劳心劳力,甚至厌倦,尽管,曾经,她们和我一样向往。”她感叹,“越深入,越深切体会到我梦想中所谓的“流浪”照进她们的原生态时,“居无定所,不断迁移”是真,“放浪,放纵,无拘束”是假,宋无名氏《异闻总录》中那一句“流浪千劫,不自解脱”才是她们的真实写照。”
看到她的《跟着戏班去流浪》后,一个戏剧工作志愿者对她说读了三四遍,每读一次都流泪。
像吉祥越剧团这样的民团,在台州有近百家,多数民团,每年演出场次在300场以上,台州已渐渐成为全国最大的越剧市场。越剧起源于嵊县,繁荣于上海,而在台州,人们惊喜地看到了中国越剧传承发展的希望。戏班人员一专多能,吃苦耐劳,既唱头肩,也跑龙套,还会“落地唱书”,深受百姓欢迎,虽在夹缝中求生存,却自有一份荣耀、一份尊严。
苏沧桑在一个月的戏班生活中,也圆了儿时“做戏梦”,扮了回小生,她老父亲给她录下了化妆、演戏扮小生到忽然笑场的每一个片段。最重要的事,她觉得自己能为辛苦求生的民间戏班做点事,纪录下一点什么,再怎么辛苦也值了。
她说,“每一次深入生活,于我都是一次灵魂的洗礼。像发现篝火的傻孩子,我大声嚷嚷,恨不得让所有人都来取暖。”
那么,有什么更深远的意义吗?她说:“多年以后我不在了,一代代人不在了,无数记录者的文字还在,未来的人读到时,依然能从中触摸到一双双人民的手,听到更接近天空或大地的声音,看到始终萦绕在人类文明之河上古老而丰盈的元气。”
“守赤子之心,接人间地气,信万物有灵”是苏沧桑的写作观。她在思考,漫漫人生,人的内心必然会经历无数次价值观的颠覆重建,文学观的颠覆重建。她发现,越是年长,越深感自己的无知,越渴望触摸探究世间万物。“万物有灵,当你念念不忘,你找不到它时,它会来找你。”这是字里字外,苏沧桑的信念。
这也是苏沧桑的梦。隐约,还觉得有不足,于是,又有了新的梦。
“我想与她们相约秋季,或者下一个秋季,或者某一个秋季,带上早已备好的礼物——一个纳米护肤喷雾器,继续跟着戏班去流浪。那时,我的想法会更少,对一些人一些事会更淡,我会更像“一家人”里真正的一员,帮烧饭奶奶烧火洗碗,帮潘香背唱词扶她上洗手间,帮赛菊她们叠戏服,帮俏俏看孩子教嘟嘟学说话写字,跟她们好好学一段戏……”
也许,她还会继续她的跟着戏班去流浪之路。
读一点
嘟嘟
夜,七点半,关帝庙戏台侧幕。
嘟嘟张着粉红色的小嘴,睁着溜圆的双眼,紧盯着正在戏台上翻跟斗的小花脸,咿咿呀呀笑着叫着,手舞足蹈。六个月大的他圆头圆脸,气质很像混血儿,穿一身红色棉布衣,肩上绣着花朵和小鸟,很好看,很干净。随着锣鼓声,他的双腿在他的母亲、25岁的小生俏俏的大腿上一蹬一蹬,一滴口水正从嘴角挂下来,映着戏台红色的灯光。
俏俏佯装很痛,哎呀哎呀的叫声被锣鼓声掩盖,光洁异常的脸庞在灯光的映照下,灿若朝阳。
这个戏班最年轻的演员,临海杜桥人,面如银盘,眉眼英武,原先主工小生,刚生了嘟嘟,暂时歇演,但戏班到哪里,她抱着嘟嘟跟到哪里,一满月就出来了,整整五个多月了。
俏俏说,嘟嘟一上戏台就会特别兴奋,半夜都不肯睡,做梦都咯咯笑。我也喜欢呆在戏班里,氛围好,开心,像一家人一样。
这句话,让我想起潘香之前说的“一家人”。
俏俏似乎不太爱笑。直觉告诉我她有心事,她自然不会说,我便不问。我想过,此番体验,不打扰,不刺探,一切顺其自然。对于她们,我只是一场路过的风。
每个做戏人上台前、下台后都会来摸摸嘟嘟的脸,他就无声地笑,也许笑出了声,但被音乐淹没了。俏俏起身替人播放电脑背景和唱词时,几个做戏人便谁有空谁抱嘟嘟,谁抱他,他都笑,将圆圆胖胖的脸和两个酒窝冲着你。我摸摸他的脸,他也笑,我伸出手抱他,他也肯。他姓金,和我一样也属猴。
一个婴儿,日夜呆在庙堂里,一点都不忌讳,如同一个已过不惑之年的女作家突然跟着戏班去流浪,都是奇怪的事。一百年前,唐诗之路上诞生了唱腔委婉、儿女情长的越剧,当徽班进军紫禁城后,南方大地上也有一群乡下人放下了锄头,开始了流浪,也开始了一个百年美梦。我没想到,第一次走进戏班走上后台,第一个遇到的,竟是跟着戏班流浪、做梦的嘟嘟。
俏俏的师傅,也就是老板娘兼小生阿朱,穿过锣鼓声前来接应我。她四十岁左右的样子,穿着套头的休闲服,没有化戏妆,两根辫子编到头顶,用黑发卡卡住。她一口临海普通话,声音柔美,有湖水的味道,笑起来露出两颗雪白的小虎牙,让人觉得很好接触。
父亲和她老公骆老板坐在台下聊天,我和她坐在戏台右侧的庙门口聊天。我表明了来意,大意是我是一个写作者,特尔喜欢越剧,不是来采访,也不一定写什么,就是想来体验一下戏班生活,如果单位或家里临时有事,我随时会回去,我会尽量不打扰他们。
黑暗中,两颗雪白的小虎牙说,你看得起我们,过来玩,我们当然欢迎,当然高兴,很高兴,你有什么需要,尽管告诉我哦。
我眼前一下子浮现黛玉进府时热情能干的好嫂子王熙凤的形象。
阿朱说,吃饭如果吃得惯,尽管跟着我们吃。被褥什么的你自己带会干净点,我们条件太差呵呵。
她又笑,戏台的侧光映出她眼角浅浅的鱼尾纹。
又聊了点别的,我问她生意好吗?
她说,戏路还好,戏金不是很高。上半年做了200场,下半年也差不多,还好,也就是挣个工资钱,演员工资一天100到400多不等,赌博戏、乱七八糟的戏,我们不做的。也不是有多高的水平,有多高的收入,常年奔波,竞争厉害,要跟各色人等打交道,很累。但我们戏班最难得的,是特别和睦,在一起十多年了,没有多话的,很开心的,很多戏路是口碑好人家找过来写戏的。
“写戏”,即外乡人过来邀请做戏、双方商定剧目、戏金、时间、地点。
吉祥越剧团其实是一个家庭戏班。阿朱夫妻掌舵,爷爷搬道具,称作“值台”,奶奶烧饭,阿朱和嫂子演戏,25岁的儿子负责灯光舞美和字幕。骆老板个子高高的,壮壮的,虽是老板,但看得出来什么事情都找阿朱商量,他接到我文广新局朋友电话后,也把我交待给了她。手里却一直拿着两罐王老吉要我和父亲喝。
爷爷仿佛是个隐身人,出入戏台搬道具像风一样自由,被观众自动忽略。戏班里,管戏服道具的“值台”或“大衣”是最辛苦的,有的终年睡在四处漏风的后台守夜。爷爷下台来就对我笑,将凳子让给我让我坐着看戏。
我之前担心他们对我的到来有顾虑或反感,但戏班里的每个人都很和气,也没有过分的热情,只有阿朱25的儿子没有笑容。
阿朱说,儿子说夏天过后他不做了。
那他做什么呢?
阿朱说,我们让他做,他还是会继续做的,从小跟着我们到处走,很听话的。
我从侧幕看过去,看到了儿时的他和今夜的嘟嘟一样,跟着戏班四处漂泊。突然想,多年后,嘟嘟一定不会记得今夜了,但还会喜欢看戏吗?
住处
午后十二点五十分,雨停了。
阿朱在偏殿宿舍的水槽前搓洗着一大盆脏衣服,化着妆,裹着头,穿着白色小衣小裤。
我问她,快一点了,你下午不演吗?
她一把关掉水龙头,边拧衣服边说,演啊,呀,来不及了哈哈哈。
她说着,将衣服往绳子上一搭一拍,小跑上坡,跑进庙里,从戏台下坐满老人的第一排前穿过去,紧跑几步跳上台阶,穿过乐队,冲到后台,拎起早就摆放在那里的蓝色戏袍和相公帽,三下五下穿戴整齐,待她挂好无线麦克风,低头套上高靴,从她公公手里接过道具褡裢背上肩,没怎么停留就站到幕旁开唱了——
“三载同窗情似海,冬生难舍玉英妹。相依相伴情意深,未知何日重相会……”
声音洪亮,气息平稳,韵味十足,演的是《藕断丝连》中的林冬生,套的是《楼台会》的曲。音乐过门后,她潇洒地一个抬脚,高靴将戏袍轻轻一踢,便走出了侧幕,走上了灯光耀眼的戏台。一个风流倜傥的小生,走进了老人们模糊的视线;而一个女子走进了古代,走进了另一种人生。
阿朱和她的姐妹们会演的戏多达一百多部,最驾轻就熟的就有三十多部,成竹在胸,才如此不慌不忙,信手拈来。
我亦步亦趋紧跟着她,最后在侧幕惊住。眼前这个光彩夺目的人,几分钟前还在简陋的住处吭哧吭哧地搓洗着一大盆脏衣服。
夜里八点,潘香皱着眉头,坐在床铺上就着昏暗的灯光背唱词,一个很旧的黄色笔记簿上,歪歪扭扭记着满满的唱词。今晚,她演《双龙太子》里的包拯,戏份很重。
这是关帝庙最靠里的偏殿后一间约十多平米的屋子,三张床铺分别用两根长凳加硬木板搭起来,铺着棉褥和凉席,没有蚊帐,床上堆了些洗漱用品、化妆品和内衣。一张旧桌子是唯一的家具,摆着两个巨大的化妆盒,两盏没有灯罩的台灯见缝插针,就是她们的化妆台。
一个很大的塑料桶,是拿来烧热水洗澡的,用热得快烧,庙里没有淋浴设备。
我说,我家很近,你们洗澡不方便到我家洗吧。
潘香笑,说,都习惯了。
墙角有一个电蚊香,靠墙有一张塌了的旧床,堆满了锅碗瓢盆瓶瓶罐罐,还有西瓜、桃子、杨梅。潘香说,是上个村子的戏迷和这个村子的头说她们演得好,送来犒劳她们的。
俏俏削好一个桃子递给我,并不叫我,只微笑着说,你吃。
我接过桃子,说,你们管自己忙哦,不用管我的。
一位70岁左右身材瘦小的婆婆正坐在另一张空床上吃苹果,她是从清港芳杜跟过来的老戏迷,她常找她们玩,没什么好玩的,就是看看她们,还有三四个清港其他村里的老太太下午来过,路更远,回去了。
潘香眯缝着一千五百多度的近视眼,吃力地背着唱词。别人演戏可以看戏台两侧的电子屏,她因小时候脑震荡耽误治疗导致弱视,全靠背下来。她身体也不太好,左腿膝盖骨有畸形肿瘤,发作起来会很痛,演武打戏翻跟斗更痛。但如果不出来做戏,老公儿子上班去了,她一个人在家呆着没意思,这里有意思。
这间房,住了她、和她最要好的小生赛菊、和赛菊最要好的俏俏嘟嘟,还有当家小旦爱妃。赛菊家近,夜里基本开车回家住,把俏俏母子也带回家。
潘香说,我们几个从来不分开的,别的戏班来挖墙脚,我们谁都不出去,我们已经是一家人。
她总是未开口先笑,眼神里透着孩子般的纯真。
短短两天,我已经听到好几次“一家人”了。在戏班里,能成一家人,是特别难得的。
一百年前,中国第一个越剧戏班在嵊县东王村出了娘胎后,不到两年时间,剡溪两岸的小歌班竟多达两百多家。艺人们沿着三条路线流浪,一是从新昌、余姚到宁波,二是从上虞、绍兴、流动到杭嘉湖,三是从东阳、诸暨进入金华,他们像吉普赛人一样,走到哪里唱到哪里,吃住都在庙里殿前,和神祗睡在一起。身体上的苦在其次,被人看不起也是轻的,最怕的是在内主角配角间勾心斗角,在外遭受地痞流氓欺压。一百年来,戏班里的人们聚散无常,更谈不上亲如一家,即使到了现在,也各有各的乱象,各有各的不易。
潘香将长发盘进发套时,微微翘起了兰花指,无名指上一个玫瑰花形状的金戒指,与包拯的形象反差很大。前一秒她还是一个女人,后一秒她就是一个男人。她说,我和赛菊约好,两个人把头发都养长,然后剪下来,做成用自己的头发做的头套,这样就又方便又自然啦。
她站了起来,说,我快上场了,我要先去下厕所。
我也站起来,说,我扶你去吧。
她说,不用不用,我自己去就可以啦,习惯啦,先戴上眼睛哈哈哈。出宿舍门,她往左,我往右。我回头看到她大红的灯笼裤、白色的斜襟小衣隐没在暑汽蒸腾的夜色里。
五 小生
当我第一眼看见小生赛菊,仿佛又一次看见了多年前坐在我家三楼南窗下一笔一笔描着眉的“他”,看见了一轮冬日下午三四点钟温柔的太阳。
这是吉祥戏班在山后浦做戏的第四天下午。
这个潘香一天要念叨很多次的叫做“赛菊”的女人正坐在宿舍的台灯下补妆,强烈的灯光将她脸上的细部暴露无遗。四十出头的她看起来只有三十岁,化着小生的妆容,面部轮廓俊朗,五官精致,眉毛和眼角均微微上扬,漆黑的双眸异常清亮,身段苗条紧致如处妙龄,黑色的蕾丝上衣、黑色的裙裤很飘逸。一个女子静静坐在一个极其简陋的场景里一下一下描着眉,散发着一种摄人心魂的静美。
赛菊话很少,只微笑着跟我打了个招呼,说,条来嬉啊,吃杨梅哦!
我说好的谢谢,你管自己忙哦。
她的声音很润朗,又带一点点磁性,仿佛暗夜里凝结了一层水雾的青花瓷。这个声音让我突然想起了另一个人,一个岁月深处曾经红遍玉环每个角落的越剧名伶,一位耄耋老人。
俏俏把嘟嘟往潘香床上一放,俯下身子在塌床那里翻找什么。潘香已经化好包拯妆,抱起嘟嘟坐在自己的肚子上,一边轻轻颠一边哈哈笑。嘟嘟一点都不害怕她的脸黑,也跟着呵呵呵笑。
俏俏翻出了一个瓶子,自言自语说,再泡点苦瓜茶喝喝。
赛菊对着镜子描眉,并没有看她,说,今天别喝了,喝多了胃寒。
俏俏说,哦。听话地放下了瓶子。
“劝妻休要泪淋淋……”
夜幕和黄梅雨同时降临时,赛菊穿过夜色,走上后台,出场亮相。戏台在漆黑的夜色里,如同夜空洞开着一扇绮丽的天窗,走马灯似地播映着天上人间的悲欢离合。今夜赛菊演的第一场是哭戏,《包公斩杨志平》中的韩世昌在病床上与爱妻话别。黑色的长发垂下半边,额上的汗珠、眼里的泪水,在夜色中闪闪发亮,哀婉的唱腔在关帝庙的夜空中盛放、枯萎。
家乡人将看戏叫做“望戏”,一个“望”字,画出了人山人海中人们翘首张望的样子。我像空气一样尾随着她,望着她,也望着戏台下一张张条凳上坐着的几十位老人,他们安静如大殿里的一尊尊雕塑,守庙人来喜站在最后一排。整个庙宇里,人神共看一台苦戏。
当我们望戏的时候,赛菊在自己的泪水和唱词里,依稀望见了许多逝去的岁月。
十年前,温岭江夏村。那天她演落难公子应天龙,用余光向戏台下望去,如她所料,又看到了那个三十多岁的卖糕女人坐在第一排左边的长凳上,痴痴地望着自己。她的身边,仍然坐着那个十七八岁、眉清目秀、衣着整洁的傻子。他和她一样,张着嘴,痴痴地望着自己。
泪水在她高亢哀婉的唱腔里纷纷坠落,人们纷纷起身,边擦眼泪边掏出几毛钱、几元钱扔到了戏台前。
一段词唱毕,戏里的“恶霸喽啰”上台来,一边叫骂一边佯装打她踢她。一根棍子眼看就要落到她身上时,突然被一个影子一把夺去——不知何时,台下的那个傻子已经蹿上了戏台,涨红着脸,撕心裂肺地嚎叫着,不要打她,不要打她!
他哭着叫着,用头和身子去撞那些“恶霸喽啰”。
赛菊赶紧从台上爬起来,戏班子人也都围上来,劝他说这是做戏,是假的,是假的。
他躺在戏台上不肯起来,放声大哭。
这时,坐在他身边的那个三十多岁的卖糕女子跑上了戏台,一把搂过他,又一把拉过赛菊,让他看她的脸、手,说,你看你看,没有受伤,是假的,菊不是好好的吗?
傻子呆了呆,突然笑了。爬起来去捡抛在台前的那些钱,捡完转身捧给她,说,菊,给你,都给你。
赛菊摇手说不要不要,眼睛却湿了。
多年后,比她大八九岁的卖糕女子也就是傻子的娘姨,成了她的至交,有了近亲般的人情往来,赛菊结婚、坐月子、造房子、过生日,她都会送来点心、七八套衣服。娘姨家造房子、儿子结婚,赛菊也去,她跟着傻子叫她娘姨,其实心里当她是亲姐姐。
几年前,玉环龙溪山里。那天她演《雪地打碗》中的孤儿周强,八岁因遭大伯母虐待逃出去讨饭,是她的拿手戏。看戏的全是上年纪的老人,穿戴都很朴素,一段唱词唱完,每位老人都起身,五元十元的,个个含泪送了一次又一次,足足送了六百多元。下台后,一位老奶奶过来拉住她哽咽着说,你演到我心里去了,我和你一样,从小没爹没妈,苦啊……
“讨饭戏”是一个老传统,一般去一个演出地都会演一场,不为图捐钱,是图彩头,也最见功夫,演员动情,戏迷过瘾。而同样是《雪地打碗》这本戏,她在另一个村里演时,却遭遇了耻辱。那天她刚唱头一句“双膝跪在大街前”,一个村干部模样的人就掏出果冻直接朝她身上砸。她气极了,站起来不唱了,那人就叫嚣着逼她唱,还要罚戏。泪珠在她眼眶里打转,却说不出一句话来。戏班里的姐妹冲出去跟他讲理,最让她感动的是台下的老人们全都帮着她们说,说他怎么可以把她当成真的要饭的?!
赛菊不知道,在离山后浦关帝庙戏台的三百米处,曾经搭过戏台,闹过罚戏。以前做戏不能唱错做错,错了就要罚戏,轻的加演折子戏,如果做漏了情节叫“偷戏”,要重罚三天戏,戏班就要亏本。明张岱就曾描述过其时绍兴演戏时“一老者坐台下,对院本,一字脱落,群起噪之,又开场重做”。
多年前,山后浦做戏,一个花旦演下楼的戏,按规矩要走13级,那天却多走了一步。以前看戏的有很多年轻人,当时一群后生起哄要罚三天戏,戏班头子和做戏人都吓坏了,赶紧请父亲这个山后浦的老知识分子去说和。
父亲被他们扶到戏台前的长凳上,站在耀眼的灯光下,说,乡亲们,戏班做错了,是不对,但他们一不是故意的,二是小错也已经认错了,三呢也加演一段戏了。大家想想,我们到哪里挣钱都难的,他们也很不容易的,大家就体谅体谅,好不好,和气生财么!
其中一个小伙不知道说了句什么,一位老人上前一把揪住他的衣襟,吼道,苏老师都说了,你还要怎样?快转回家去!后生们也就散了。
如今,看戏的年轻人几乎没有了,老人们没那么精明也不计较,罚戏自然也就没有了。但赛菊每一场都全情投入,更不允许自己出错。她们来山后浦第一晚演的是《双杀嫂》,没下雨,来的观众多,纷纷叫好,第二天下午演《丞相试母》,观众反应又很好,地方上的头闻讯很开心,买了几十斤桃子、四个大西瓜送给戏班。赛菊忙得一口都没吃,但心理上很满足。她想,我就是戏里的丞相施文青,观众喜欢这个戏,说明我演活了。
有那么一两分钟,后台只剩下我一人。我忽然发现挂着皇帝帽的架子下的神位前点起了两支红蜡烛。我知道,又有老人“戏刹”了,也就是传说的看戏走火入魔了,身体不舒服了,解药就是到戏班后台点上蜡烛拜拜神仙老爷,来不了的就差人剪下一点皇帝帽的流苏烧成灰喝了就没事了。有用没用不知道,戏班却总是有求必应,让看戏人图个心安,就像故乡人说的,高丽人参太补,邪关住了,要用萝卜解。
在后台,我不敢乱走乱动,随便问话,怕犯了戏班的禁忌。小时候就听说,不能问帽子重不重,不能问嗓子好不好,身体好不好,这些都关乎做戏能否顺利,关乎他们的平安,因而外人宁可信其有。还比如,鼓板是乐队的灵魂,打鼓板的师傅叫“鼓板佬”,他坐的地方叫九龙口,是戏台上最神圣的位置,其他人决不允许坐,更不允许触摸鼓板。
此时,小旦爱妃上台,赛菊退到后台,从贴着一个“赛”字的戏箱里取出一条绑带绑上头,侧过头对我笑了一笑,眼角还挂着一滴晶莹的泪。
再过一个小时,戏散后,她会开车回到距离此地十公里的漩门湾大坝老鹰窠的家,那是一个靠海的小山村,大坝未筑成时,传说连飞鸟都飞不过去。到家后,她会煮两碗面给自己和俏俏当夜宵,然后帮俏俏给嘟嘟洗澡,睡下,第二天中午吃了午饭再赶过来化妆。
这个在古代和现实之间自如穿越的女人,她在海边的家是怎样的?她的丈夫是做什么的?在家里,这个优雅神秘的女人是什么样子的?她对我这个一直尾随着她的不速之客是怎么看的?
多日后,我看到她在微信里这样写道:第四天下午演《藕断丝连》,我演林天赐。下半场还在化妆,来了非常非常难得的贵客苏沧桑老师。我们小小戏班迎来大作家,心情无比兴奋[憨笑][憨笑]
然而,当时她那么沉静,甚至有点冷淡。
苏沧桑,女,1968年出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毕业于杭州大学,现就职于浙江省作家协会。在《十月》《人民文学》、《中国作家》、《散文》、《美文》、《散文选刊》、《读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300余万字,出版散文集《等一碗乡愁》等多部、非虚构文学《守梦人》、长篇小说《千眼温柔》等。曾获“冰心散文奖”、“中国故事奖”、“首届全球丰子恺散文奖金奖”、“琦君散文奖”等。多篇作品入选全国各类散文选集、散文年选、排行榜,并被应用于中、高考试题,入选各类教材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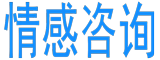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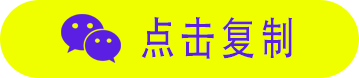




评论列表
老师真厉害,耐心而又理智的去帮助受伤的人,文章写的让人很感动
老师,可以咨询下吗?
求助
如果發信息不回,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