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名家侧影”栏目由《时代文学》1997年推出,先后由何镇邦、白烨、贺绍俊等人主持,每期选一位名家,并请几位同好、老友从不同角度畅聊其人其文,让读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作家在作品后面的鲜为人知的故事。二十余年来,100多位当代中国作家,500多位栏目作者,在这个可以从容成长一代人的时间里,以各自不同的姿态与读者相见,并在文学史上留下璀璨星光。有鉴于此,中国作家网重新推出“名家侧影”系列,精选其中文章,一起听文坛上的老老少少聊文人,话文事。

刘震云
随着刘震云的《塔铺》《新兵连》一炮打响,“一下子就红了起来”(李国文语)。一个时期,他的作品,如《单位》《一地鸡毛》等,成了新写实的代表作。
刘震云为文可以说是不老实的,老是在探求点新的东西,变出新面孔;但他的为人却是诚实的,且是一以贯之的诚实。对师长,对朋友,对同事,都是一个“诚”字,当然,他仍然有点嘎,有点“油”,有点狡黠。因此,关于他的“花絮”,被传诵也不少。
在这里,我们约请他的老师、同事和同学一起来聊聊,就是为了满足读者们了解刘震云的愿望。
我对世界所知甚少
刘震云
不仅仅是年龄关系。我还没有达到对自己发生强烈怀疑的阶段和境界——怀疑的指向往往还是外在世界。但我分明看到自己的过去和作品变得陌生了——像困兽一样躲在阴凉的角落瑟瑟发抖、迷惑不解地看着我。相互的爱怜和同情油然产生。我们相互抚摩着知道自己对世界所知甚少——这个世界、人的世界、人的内心世界、凌驾于内心之上的情绪的翻腾和游走及白天和夜晚的区别,以及你怎么控制你的梦特别是白日梦,当然还有永远不可触摸的万物生灵相对你的情感流淌方式。当我们想起我们曾经蜷缩在对世界的误会的自己的投影里沾沾自喜时,我们除了无地自容更想做的是失声大号。你比以前脆弱多了。想起温暖的朋友和往事,还有那些冰凉的现实,当你们想聚首一隅相互诉说时也往往是一语未终,潸然泪下。甚至你对往事的真实过程发生了怀疑。你变成了一个存在主义者。你对许多简单的话语想作幽远和深情的注释。你周围的世界和情感像风雨中的泥片颓倒一样在飞速地解体和掉落——你试图挽留它们或是在梦中抓住它滑溜的尾巴但梦醒时分你发现留在原地的只有你自己——虽然你留下一把岁月的青丝那确是一把好头发。虽然你的亲人每天都在说汉语,但你对汉语像对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其他语言一样所知甚少。你有些口讷和犹豫,你不知道将自己的脚步放在灶台的什么位置合适——所有的人和语言在你面前都变得陌生。你掉到荆棘棵子里浑身挣扎不动的时候你只好浑身是汗地挣扎着醒来,大梦初醒的时候往往太阳正当头,别人告诉你这就是正午。
我是一个业余作者。我幻想不久的将来我能成为专业作家,用写作挣的钱来养活自己。这才是一个人在现实光彩的开始。
开始一朵乌云
迟子建
刘震云是我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时的师兄。那所学院位于京郊十里堡,只是一座矮矮的瓦灰色小楼。校园只有几棵孱弱的杨树和一片还算茂盛的藤萝架,常见震云和做律师的太太抱着美丽的女儿妞妞在这简朴的校园里徘徊。刘震云家所住的《农民日报》社离鲁迅文学院很近,他家没有花园,便把校园当成自家花园来闲逛。
刘震云来校园闲逛时多半是黄昏时分。白天在教室里却不常见他,他在《农民日报》社还有一些事务性的工作要做。只要他来教室,通常是提着一个大水杯,下课休息时就去同学的宿舍续水,有时也顺便蹭一支同学的烟来抽。
刘震云喜欢开玩笑。他开起玩笑来不动声色,同学们对他的评价是:“刘震云的话永远让人辨不清真假”,所以即使他说真话的时候也没人把它当真。他的性情如同他的名字一样,沾染了一些云气的氤氲与逍遥,当你认为看清他时,其实他还十分遥远。
刘震云走路有些仄着身子,看上去就像个农民劳作了一天从田里归来,他的一口纯正的河南腔还带着那块土地的麦场被夕阳灼过的气息。常听他谈起外祖母,他对她非常敬佩和热爱。记得有一年春季他外祖母去世,他从河南老家奔丧回来,他在电话中很伤感地说了一句“我有大不幸了,我姥姥去世了。”那一瞬间他委屈得像个孩子,好像他外祖母领着他出去拾麦子,不负责任地把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给抛到野地上了。
毕业之后见刘震云的机会便少了。倒是常在电视上看到他在做各种节目的嘉宾,还“很恶心地”在《甲方乙方》中过了一把电影瘾,饰演了一位失恋者。刘震云在电影中的表现可以用一部名著的篇名来概括:被污辱与被损害的。刘震云是一个清醒理智的人,但这一次却是把戏做过了头。当我这么说他的时候,他很理直气壮地辩白:“葛优说我没准能拿个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呢”。我想这是刘震云接受批评的一种表达方式。
刘震云苦心经营了八年的鸿篇巨制《故乡面和花朵》终于杀青了,我还没有看到这部长篇的全貌。他的毅力和才情令人叹服。我和毕淑敏有一次聊起刘震云,毕淑敏说:“刘震云可真了不起,能够写一部这么长的小说。”我想只有年富力强的男作家才会有这种魄力接受这种自我挑战。漫长的写作对作家身心的折磨是不言而喻的,而它带给作家的那种畅快淋漓的艺术感觉也是不言而喻的。
刘震云是个看上去很舒服的人,极易接触,所以他人缘不错。他的身上既有农民式的淳朴,又有农民式的狡猾,而这也仅仅是一种直觉。何镇邦老师勒令我写他时,我以为对他很了解,可一落笔才知道刘震云对我来说还是相当陌生的。要画出一个活生生的他,恐怕只有王朔才会胜任。
记得有一年一帮朋友去黄山参加笔会,途经太平湖时,那些会游泳的人纷纷跃人水中。我们这些旱鸭子坐在湖边看绿水中的人姿态万千地浮游,大多数的人都把身子浸在水里潜游,只有一个人是一直漂在水面上的,就像一具浮尸。大家惊异地指点着那个人时,他渐渐地由湖中心向岸边游来,我们看到这个泳姿怪诞的人就是刘震云。坐在岸边的人就拼命起哄,让他不能上岸,刘震云不动声色地又朝湖中心游去,依然用他那自由而又有些骇人的泳姿,一个朋友骂他:“装死!”
但愿刘震云能够做一朵乌云,当闪电击穿它时,会散落倾盆大雨。没有雨意的云彩只是晴朗的一种点缀,而乌云却能在天地间制造一种独有的气势和声音。
刘震云在单位里
沙 丘
刘震云的《单位》写得好,而他自己在单位里又怎样呢?
超脱的“官人”
震云当官是1991年春天的事。他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农民日报》社工作,担任编辑、记者。这一年报社领导更换,机构调整,让他来副刊部当部主任。他轻而易举地当了官,并不像他的小说《单位》《官场》《官人》中主人公们那样煞费心机。
在这之前,他不曾尝过当官的滋味儿。读书时连小组长也没当过,只在部队做过一段时间副班长。这回一下子从普通记者蹦到处级,他没想到这样顺。
家乡的人们重视职务,过去看他多年在外只混到个“青年作家”,看不起他。如今开始刮目相看了。但是单位的一些同事则认为,一位有了相当影响的作家在这些“俗务”上花费工夫,有点得不偿失。震云仍把主要精力用在写作上,但绝对乐于参与报社的重大报道,也愿意和“弟兄们”一起“热闹”,所以他不仅接受行政职务,最近还领了党支部书记的衔。
为什么要取得某些方面的成功,就必须抛弃另一些东西呢?人一生应当有的都应当有,这是强者的态度。作为作家的他把一切生活内容都当成体验,当然也不放弃当官的体验。震云是智者,他同样需要常人需要的东西,但绝不让它成为自己的负担,他巧妙地驾驭环境而不为它所累。
我曾经问他。当部主任影不影响写小说。他说:“没啥影响,王蒙开完会,马上可以坐下来写小说,这是作家必须具备的心理调节能力。再说每天写字不过几个小时,我也不必故作特忙,既然领导让干,那就干吧。”
震云也因为做官而变得更加谨慎:“如果我矫情,大家就不会买我的账”,他心里有数,“一些作家朋友同环境不和谐,说单位总找自己的毛病,其责任多半在自己。不要以为写了点东西就比别人高明,行业之间没有贵贱之分,如果想让别人尊重自己,自己首先要尊重别人。”
“我没有其他本事,只会写小说。”震云说。然而他做起官来却很在行,大事清楚,小事糊涂,有些事则故意糊涂。只要事情的大体走向对了,过程中出点问题没有什么;争大不争小,他很少同人发生争论,但是必须力争的事就不讲情面。记得他有两次发脾气,一次因为调人,他骂得很厉害,当着很多女士的面骂;还有一回为了编辑的稿子骂有关部门。
他在部门工作上,不求轰轰烈烈,而是采取无为而治的方针。求个安静,求个宽松,果然大家处得很和谐。要么不做,既做就要好;不求数量,但求质量,出影响,同他写小说的路子一样。
几十位名作家撰文的《名家与农村》,呼唤新游记的《心系旅途》,宁缺毋滥的长篇连载《陈永贵沉浮中南海》和《浩然的夫妻生活》,编辑下农村体验生活每人一篇散文的《北京人在李堡》都是这个期间副刊部的拳头产品。
冷面热心
震云看上去有些冷,他性格内向,不喜言谈,很少同人交流,如果不找上门,他是不轻易涉及“文学”二字的。好像不屑同人交谈似的,至于文学界的活动,他总是悄然来去,谁也不知他在做些什么。
“每当我对周围环境烦躁不已时,我就像阿Q一样狠狠想:别以为我活在你们中间,我的心不在这里。”他在《文汇报》上发表这样的“创作谈”更使人对他敬而远之。
距离是存在的,这是他同环境的关系。
“悄悄地做事更加重要,”他说。他喜欢海明威的一句话:“小说好像浮在海面上的冰山,只露出三分之一,三分之二全在海下。”“这种冰山往前移动是很有气势的。我不喜欢一块冰浮在海上,那样只能是块冰,会很快融化掉的。”
你只有长期相处,才能慢慢了解他。
冷静内涵,睿智机敏,性情温醇随和,重义气,也很富于人情味。念念不忘养育自己的外祖母,喜欢一个人陪她说话。八小时之外,大多时间泡在女儿身上。他的作品很多是由友情的触发而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扉页上就标明:“此书献给我的外祖母。”
震云并不擅唱歌,更很少登台,可有一回在歌厅却为一位女士献了歌。编辑孙丽娜心高而体弱,视力也不好,常为力不从心而叹息。住进康复中心,过节不能回家,大家便聚齐去探望她。邀她出来,点她爱吃的鱼,然后去找歌厅。那天震云带着孩子跑了很多路赶来。本来大伙只想听听别人唱,随着音乐跳跳舞,不料震云第一个上台操起话筒大声说:“我唱一首,献给孙小姐,祝她早日康复!”“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唱得小孙哭了,大家听了也很感动。
总是与人为善,总是成人之美,乐于帮忙。我对他最早的印象是他刚到报社不久,我购置了沙发正愁没人帮忙抬,他路过一看,就主动帮我抬上楼,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我心里很感激,心想小伙子真朴实。周末版老郝发病住院,震云听说后,邀我同去探望。编辑冯雷的父亲去世了,我们商定去慰问,还派人送过一些钱去。临到向遗体告别,我说咱们隔了一层关系,不去也罢。震云说:“还是去的好。”
“快去,单位开始给装电话了!”有一天他提醒我,好早点把这事办了。他还告诉我穿老头鞋好,他自己有时跟着去开编前会,说穿着舒服,建议我也买一双。
文人相亲
他在同事当中爱称兄道弟。这回杂志约稿,我问从哪个角度写好,他说:“你就写咱们兄弟的相处吧!”记得他第一次赠我他的书,签上了“吾兄指教”。平时也总是“兄长”挂嘴边。国人讲究长幼之序,兄是一种尊称,男人社交上的客套,通常没有严格的年龄概念。但我感觉到他不是一般的称呼,而是发自内心的。理解人、尊重人是他一贯的做人准则,我们合作三年没有发生过任何“过节儿”,同他这种态度是分不开的。
尽管性格上有共同之处,但处理事情的路数,一个是作家型的,一个是编辑型的。他是举重若轻,我是举轻若重。我极力调整,还是常常不知不觉陷人琐碎的事务之中。“你总是过于具体”,他自己超然,也希望我超然一些。
有一次我们谈起写作,不经意地聊,聊《红楼梦》《追忆似水年华》……我说到自己的困惑,在报纸上写的东西同杂志上的不一样,没把握,不知这样写行不行。他说,刊物其实很需要这样的东西,“没把握”往往正是出好东西的时候。当时还有几句溢美的话。我似乎觉得自己有希望了。我同他探讨写作仅此一回,却大有“胜读十年书”之感,可见交流不在于多寡,也不在于形式。
1991 年底我出差广东、海南,《心系旅途》专栏刚开不久,缺稿了,震云对我出差很高兴:“带上电传机,随时发稿子回来!”我怕丢,没带。南行一个月,回来陆续而成15篇。震云很高兴,请汪曾祺或何镇邦等名家写评论,一方面为了打响专栏同时也为我好,结果是何镇邦写的。
我有幸同他搭档,一块儿搞副刊,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潜移默化地受他影响,明彻了许多生活的真谛,我开始从烦琐的生活困扰中跳出来,变得洒脱一些,自我一些了。平心而论,我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是从那时开始的。
然而震云的写作却早得多,他起先是在二楼空荡的机动记者部,后来是在五楼副刊部的一个独间里一笔一笔写出了《塔铺》《新兵连》《一地鸡毛》《头人》等七部中篇和两部长篇,在单位里他第一个掷笔换了电脑,写出中篇《新闻》。
今年春天我奉命去另一个部门任职,要离开工作了好几年的副刊,有些留恋。震云很高兴,立刻设酒送我,我明白他的心思,是为我的一些事情着想。
写字的俗人
单位盖宿舍楼,需要搬迁。人们才发现一排平房后墙根冒出的一丛小榆树,长到胳膊粗了。看到它,我联想起震云。
同是报人,很多人庸庸碌碌,而他却悄悄地成功了。震云随着文学而成长,随着单位而成长。有一回,我约了部里同事去单位的近邻鲁迅文学院听过他一场讲演。“震云的讲演,我们应当去听。”我对部里的同事说。这次去“鲁院”才知他活跃于社会已久,他经常被他的导师何镇邦叫去为学员们讲演。他不带讲稿,文采飞扬,谈笑风生,对他的见地和口才我们始料不及。
十年磨砺,文学使他一举成名,也使他在单位获得成功。平时他依然悄悄地走路,静静地说话,微微地笑。没有成功者踌躇满志的样子,没有现代青年时髦的口语和衣着,也没有一些作家总是高人一等的派头。而是越来越默默无闻,越来越老到。总是蒙眬着眼睛,很少高谈阔论。他总是以“写字的俗人”自居,将自己的大事化小。出国交流回来问他感受,说:“就像出了趟远差。”
“严肃和俗都具备了,才是完整的人。写字就是写字。写字之余再来谈写字就显得有些做作和可笑。写字之余干些什么呢?调皮和读书。”他曾这样写道。在平时,他还热衷于同事们的热闹场合(聚餐),不计较饭馆档次;对“女朋友”和“有贼心没贼胆”的话题特感兴趣,而且关心对方的长相。
“她,漂亮吗?”一次大家研究一个人的调人时,震云这样问。
喜欢电视剧《一休》和《猫和老鼠》。喜欢穿肥大的陈年绿军穿老头鞋,留恋一件被风刮走的旧背心。
午饭时间到了,妻子电话打到办公室,他便下楼去食堂同她共餐——看来关系挺和谐,这时别人就不便凑近那桌子。如果只他一个人,便打饭回家。迫不及待地边走边吃,可能是包子之类;碗举起来,头仰得很高,可能是汤。
傍晚时分,办公楼前的空地便成了他和女儿玩耍的场所(宿舍在单位)。是妻子分派的还是主动承揽的,没有问过。有时光着膀子玩得汗流浃背,同过往的熟人打招呼“吃了吗”。时常是坐在台阶上默默地看着孩子玩,无思无虑的样子。如果有画家画下来,一定是他最好的画像。
杂说震云
何镇邦
一
1988年初夏,我当时在鲁迅文学院正起劲地做着同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第一期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筹备工作。刘震云那时在《农民日报》当机动记者,并已发表了短篇小说《塔铺》和中篇小说《新兵连》。记得他常于晚饭前后到鲁院来串门,或与学员们一起打打篮球,或抱着他不满周岁的女儿,穿着拖鞋到我办公室聊聊天。有一次,我们还郑重其事请他同当时正在校学习的第四期文学创作进修班的学员一起座谈,介绍他的创作经验。也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他得知我们筹备创办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消息,他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和热情,在八十多位报名的名单中,就有了他的名字。以他的创作实绩和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的学历,我们自然优先录取了他。但因为他工作后住在《农民日报》社里,离鲁院只有几步之遥,无须住校,而他的工作是机动的,也无意脱产,于是就成了我们第一期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一名比较特殊的学员,也就成了我的学生。
震云还真是个好学生,他往往比某些住校学生还遵守纪律,按时来听课,参加一些班里的活动,只是不卷入班里某些是是非非而已。他还是那么谦逊,不只对老师,也对一般的员工。而且在鲁院学习的这两年半期间,他在创作上也有很大的长进。稍不留神,他在刊物上相继发表了《单位》《头人》《官场》《官人》《一地鸡毛》等一批引起相当反响的中篇小说,成为当时正在红火的“新写实”的代表作家之一,还写出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成了班上创作成绩最突出者之一。作为他的创作导师的李国文,也常常称赞他的创作,并给予他的《创作理论与实践》课以高分。
震云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在研究生班里完成了他的学业,修完了各门课程。学完了 30多个学分,拿到了研究生毕业证书,只是不知为什么,他不愿意撰写硕士学位论文,不申请答辩,当然也就没有拿到学位证书。估计他已有大学本科毕业文凭,也在不久之后被评为一级作家,就不想去费这个力气了。
二
从研究生班毕业后这七八年间,他发表的作品的量好似不如在校学习那几年。这大约一方面是由于他担任了《农民日报》文体部主任,有了一定的责任,不像原来当机动记者那样自在,也不像在研究生班读书时什么都可以用正在读书的名义往外挡;另一方面他是把绝大部分可以用的时间用于那部长达两百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故乡面和花朵》的创作上去了。这部长篇的写作可能开始于研究生班的后期,坚持写了八年多,有一次在他的办公室里聊天,发现他的桌上有一本硬皮封面十六开的大笔记本,一问原来是此部长篇的初稿。他打开给我看,每一页上都密密麻麻地写着,又有些改动的符号他说写过这么一遍后,才往电脑上移,然后又在电脑上改。在文坛上时兴传媒热炒,作家们都浮躁得可以的时代,震云能耐着寂寞,坐在他那间放了电脑的办公室里,从大本子到电脑,整整地耕耘了八年多,仅就这一点说,就很不简单。而且这八年多。也正是他很火的时候,他能谢绝各种稿约,潜心于长篇小说创作,更是不简单了。
当然,在写《故乡面和花朵》这八年多的时间里,他也还发表和出版了一批新作。诸如第二部长篇小说《故乡天下流传》,中篇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新闻》,还有写得很别致的短篇小说《土塬鼓点后:理查德·克莱德曼》,等等。读到1994年发于《长城》上的《新闻》,我就明显地感到震云的创作路数在变,从《一地鸡毛》《单位》那种写生活的原生态,那种追求生活的精细逼真的“原生态”到把生活荒诞化,把人物符号化。当时读后颇激动,还同震云通了电话,本来是想写篇评论来评论一番震云创作上的这种变化的,而后大概又忙什么别的去,顾不上写这篇文章,于是就过去了。今春以来,陆续读到他的长篇《故乡面和花朵》散发在各种文学期刊上的片段,才发现《新闻》的写作路数的变化乃是《故乡面和花朵》新路子和新风格的先兆,我很后悔没有抓紧时间写好那篇关于《新闻》的评论。
三
在鲁迅文学院这十多年的教书生涯,使我有机会认识了各种各样的文学青年,以至各种各样的想靠文学混碗饭吃的人,眼界于是大开。据不准确的统计,十多年间,在鲁院的课堂上听过我的课的可称为我的学生的大概近千人,而其中两期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和两期文学评论研究生班的学生就有一百五十多人。这个数字里,当然不包括那些在社会上或在别的大学里听过我的课或文学讲座的人数。如果加上他们,当然是一个更大的数字。这些年来,我常为拥有这么多听过我的课的学生而欣慰,也常为这么多学生给我找来的种种麻烦而苦恼。有人开玩笑说我的桃李遍天下,走到哪里都不会饿着肚子,这是确实的。如今走到哪儿,常能遇到我熟悉或不怎么熟悉的学生热心照料或招呼自己,这是一种从事教育工作的独有的乐趣。但既然“桃李满天下”,那在那么多的桃李之中,就既有甜的,也有酸的、苦的和涩的。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文学青年中,相当多都很敏感,也很自尊,是很容易得罪他们的,与他们打交道是颇不容易的。有时候为他们做了九十九件事,他们也处处表示感谢,但只要一件事没做好,他们就不满意,甚于可以诋毁你。于是,我同我那么多的学生们打交道,是时时很小心,甚至有时是提心吊胆的。
但是,在我的学生中,也有一些是可以交朋友甚至交心的,我同他们之间不仅是师生,也是朋友。在这种可以称作师友,可以交心的学生中,就有刘震云。
尊师是一种传统的美德,震云之对于我,不仅是一般尊师意义上的尊重,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朋友的真诚。有人说他嘎,且有点“油”。照我看来,他不仅创作上很机趣,很有幽默感;在生活中,在处理人事关系中,也很机敏,可以说是表面上憨厚朴实下的一种机智和狡黠。这对于一个远从豫北农村到京城里来闯天下的青年人来说,是必要的。从我同震云十多年的交往中,我更多地体验到的是他的真诚和朴实。我们之间固然有出于礼貌的相互尊重,但更多的是出于真诚的交流。当年,我因工作关系有时住在鲁院办公室,晚上常想喝点粥,有时就跑到震云家去喝。有时,他还会添点菜,例如在熬了小米粥和准备点烙饼、青菜之外,还临时从市场上买来一点烧鸡什么的。尽管他和他的爱人小郭并不怎么精于厨艺,做出的菜实在不敢恭维。但我还是很乐意到他们家去喝粥,去感受他们家庭中那一份温馨。有时,震云也同我商量他的工作。1991年夏,他从研究生班毕业不久,报社的机动记者部撤销,报社领导拟安排他去当文体部主任,他开始还有点犹豫,怕影响创作。他同我商量时,我鼓励他去当这个主任。我当时坦率地告诉他,报社给他房子住,发给他工资,如不给报社工作,人家是不可能白白养活一个作家的。他采纳了我的意见,很痛快地应承下来。走马上任后,一方面大胆用人,让手下的人去干;一方面又对版面进行改革,既不太费心,又收到功效,足见其大将风度。
这一点强过我辈。当然,我们也是支持他的工作的。例如他当了文体部主任后在副刊上开辟的专栏“名家与农村”,我和我的很多朋友都为之写过文章,王蒙还一气在这个专栏上发了两篇,第二篇《我爱喝稀粥》还引起方方面面的关注。不过,说老实话,震云当文体部主任,我们又多了一块阵地,有些文章就可以到他的版面上发,有时也可以到他那儿混顿饭吃吃。这也是我怂恿他去当那个主任的一点小打算,如今从实招来。
四
震云之对待同学和朋友,也是很真诚的。前年才听到他的一位研究生班的同学说到一件事,很使我感动。还是在研究生班预备班的时候,同班的一位同学因为三千元学费而犯了难,震云知道后毫不犹豫把仅有的三千元存款取出来,借给这位同学交了学费。要知道,震云当时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仅有的一点稿费收人,要抚育一个刚刚周岁的女儿,还要招待常常来北京打扰他的乡亲,拿出三千元来借同学,实为一桩壮举和义举。但他做后从不声张。这就是震云的脾气。
不仅是待人,就是在对待自己的创作上,他也是不喜欢张扬,更不用说通过各种门道去热炒自己的作品了。在我的记忆里,震云从来没有开过什么作品研讨会之类的,也没有找别人写过自己的专访和在报纸上到处发照片。他的作品是靠它们的艺术质量走向广大读者,而被广大读者所认同的。当然,他也希望听到别人对他的作品的意见,有时也希望我为之写点评论,但从不在乎。不像有的青年,常常在乎一篇或几篇评论,甚至对不给他们写评论而耿耿于怀。震云的这种既在意又不在意别人的评论的态度,也显示出他的一种大家风度。
当然,我和他的一些朋友一样,弄不清楚震云为什么要在电影《甲方乙方》里串演那么一个角色,也弄不明白他为什么既然安于坐冷板凳,却时时出现在电视荧屏上,大侃什么盗版图书和被人支使去谈论各种话题。这大概是聪明的震云的另一面。人生活在这个缤纷五彩的社会里,大概是需要几副面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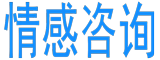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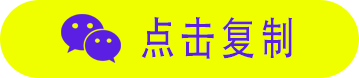




评论列表
情感分析的比较透彻,男女朋友们可以多学习学习
求助